小说家孙智正,有一个“用文字复制一生”的计划
哲学家萨特有一本薄薄的书,名为《文字生涯》,是作者关于童年生活的小说。 小说家孙智正多次对来访者说有“用文字复制一生”的计划。 用文字原原本本、事无巨细,再按时间顺序复制人的一生……这也许是只有妄想家才能想起、只有创造者才能做到的事情。 孙智正的不可思议和“胡说”可能就在这里。 现在他是能量不足的人。 据他的朋友们说,即使是白天,孙智正也必须每隔三两个小时休息一次。 他说的休息就是躺着,闭着眼睛睡觉,是真正的休息。 在那之后,继续他的生活和工作。
很久以前他没有正式工作,和妻子、儿子住在北京郊区。 他的工作是生活和写作。 他的“不可思议”计划曾被认为难以实现,但他用自己的手写了他的心,并在他的文章中付诸实施。 他的《句群》 《史诗》、长篇小说《青少年》和《南方》可能就是那样的作品。 小说家——、现在已经不能叫“小说家”了,还是叫作家孙智正,干脆发明一个新名词来定义和称呼他? 但是,就像有人说或本人说的那样,“我没那么重要。 我不需要单独的语言”。 但是,听说他也说了。 据说他最渴望的是占有语言。 这也是自古以来众多诗人、小说家、哲学家的愿望。
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与周围的一切和自己的思想打交道。 就连国王也不例外。 ——口吃的国王也要学会说话。 即使当众演讲——,也不能代替别人生活。 另外,你也不能代替别人讲述自己的生活。 根据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讲的关于人与万物命运的神话,一个人现在的生活是他过去的——前世,通过自己的福报、运气和个人的选择得到的。 我们每个人经过过去女神、现在女神,特别是未来女神之手见证的生活是独特的,无法回头。 可能没有人见过另一个人完整的人生。 即使是自己的父母和孩子,有些事情也会在别人面前被隐藏,或者被忘记。 ……如果作家孙智正有这样的愿望和决心,作为他的朋友和读者,我会祝福他写的书,并尽力去审视。 最终,被称为“日记”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到的马塞尔想写的《像《一千零一夜》那样长的书》——的完整而唯一的书,是有一天他提到的“更长寿的人”对话|孙智正严彬
“我想成为有独创性的《永远》作家”
严彬:几年前,一家电商网站卖了你的《南方》,才几元钱,好像9元以上。 很美。 适合给某个朋友。 首先谈谈《南方》这本书吧。 这部600多页的作品是怎么写的?
孙智正:那个时候出版社好像在整理库存,但是没有买。 现在在旧书网站上卖得比原来贵多了。
我写完了《青少年》。 我已经好多年没写长的东西了。 我有“用文字复制一生”的想法,想写《童年与少年》。 那个结束正好是《青少年》的开始。 内容当然有我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但会找到一个形状。 我试了好几次,突然觉得把所有的事情、事情原原本本地罗列出来就好了,这就是“形式”。 所以像《南方》 (那是《童年和少年》 )草稿和未经处理的素材一样,你可以在一页上看到很多不相关的事情和事情的排列。 当然那还有线索。 是我把这些事情、事情按线性时间排列的。 无论科学对时间的认识如何发展,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时间是线性的对人来说是最自然的。
还有,《南方》使用的浙江嵊州方言很多。 从发布信息的观点来看,我反对使用方言,但我陷入了“啊,方言的这个发音是这个字吗?”的惊讶感。 另外,虽然有写作以外的想法,但我觉得方言反而更容易被主流理解和接受。 因为它给了“方言写作”一个把手,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自己。 这样的策略要说策略,我认为不影响我写作的本质。 我这么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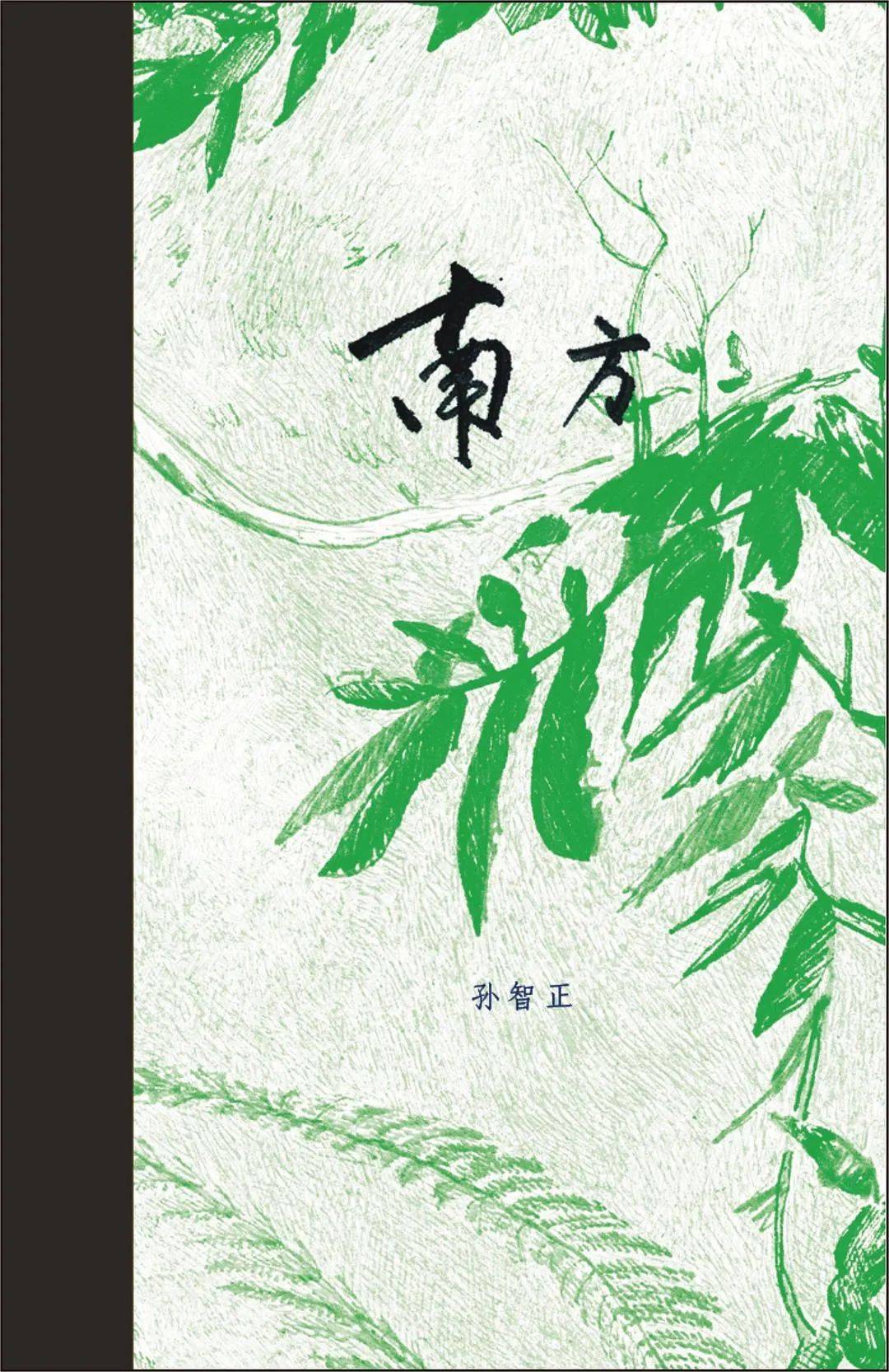
《南方》,孙智正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年9月
严彬: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朋友圈,江苏和浙江(你是浙江人)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的时候,像赵志明、崔曼莉、你啊,以及和你们关系密切的一些作家,比如乌青、竖、司屠、李红旗、河南驻马店的郑在欢,前辈作家韩东、朱文等……感觉你/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个性和集体性,相近的趣味和个性,共同的朋友和故事,讲不完的南京北京生活……不知道你怎么看。你心目中有没有所谓“南方作家群”或者文学友谊?你觉得自己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孙智正:我觉得没在一个集体里啊。可能我比较喜欢跟人待在一起,以前身体好时经常和大家在一起吃饭、打牌,现在也在打但少了。我通过小平(赵志明)、张羞认识了好多写东西的人。可以说,我在北京的饭桌上重新上了一次真正的学。
如果要说我跟哪个集体比较近,那应该是“橡皮写作群”,但我应该是远亲绝不是嫡系。还有你说赵志明在里面的江苏的或者就是南京的集体,那我应该离得更远但也近,有的朋友把我拉黑了,有的朋友把我屏蔽了,这都没关系,如果说我和橡皮的理念基本趋同,和南京的写作者们应该有一半是相通的。我知道,从骨子里来讲我们互不讨厌,知道大家基本上是一路的。有时我很羡慕有集体的人,因为这样可以互相扶持,做事情顺利些,也可以解决一些表面的孤独,但我确实是在集体之外的。这不是怎么样好怎么样坏的价值判断,是一个你是怎么样的事实判断吧。
1.公园里的椅子
街边有一个狭长的公园,里面摆着一些椅子。其实这应该是个绿化带。我沿着外面的水泥路由北往南走,椅子上都坐着人。这让我很失望,最失望的那次是上次,由南往北走,我已经在绿化带里,沿着弯弯曲曲的水泥小径走,没有料到椅子上都坐着人,一些情侣,好几个听收音机的老头,还有一些光是坐着的,这些都是铁椅子,摆着北京的露天底下,积满了灰尘,只有在椅子的中央地带被各种各样的屁股擦干净。
等我一直走到那个乒乓球场时,才看到里面有几把椅子空着,很多人在打乒乓球。我在入口处的第一把椅子坐下来,很舒服地把背一靠,两腿一伸,打开书开始看。看了不到一页,手指上落了一点雨,我疑惑地抬头看看,头上是树叶,我想会不会是鸟屎,看看手指上的水迹很干净,就放弃了想闻的念头,可能是树叶上的积水滑落下来。
过了一会儿,快看完第一篇了,越来越多的水滴落下来,不过还很疏。我听到有人说下雨了,不过打乒乓球的人都在打。我也继续看,突然雨滴密集起来,书页打湿了。我站起来往回走,雨越来越大,很多人躲在商店的屋檐下,有些人钻进车里。我只好往回走,赶回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快要开始了。虽然我很喜欢下雨,但我不喜欢在路上的时候下雨。空气里充满了干燥的泥土气味,如果在草地上,这样雨中的气味应该很好闻吧。前面有人在搬家,路边堆满了红色的沙发,我想起,这附近是有家酒吧的,有把沙发上面放着一本《三联生活周刊》。
那些刚才坐满人的椅子现在都空着,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不过我也不会去坐了,虽然我很喜欢坐到椅子上,但不喜欢坐在那里淋雨,雨太凉了,如果雨足够大,就会把那些椅子冲刷得干净一些,你知道,坐到一把很干净的铁椅子的感觉很好,如果雨不够大,就只会在椅子上留下点点水斑,就像铺在桌面上的面粉,落满了水滴。
2006.6.10
严彬:读你的作品,比如《句群》中一个文末标记2006.6.10的段落,你写下了一段平淡无奇的一天中的一个片段,这样的片段转化成日常生活,几乎每个人都以相近的方式在过着,在经历,不存在的时间如水一般逝去,谁也没有想起要在那样的日子里抓住些什么。而你为那样的一天写下了属于它的一段,你将它命名为《公园里的椅子》。你的行为和作品看似是写出了你的生活,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来自个人经验的作品,这个作品很明显是“反常”的,不同于我们认知的文学作品,小说或散文,当然像是日记——可几乎没有人将日记视为自己的作品,更不用说是文学作品。它包含了个人的日常经验和世界曾经如其所是的一个四维体,一些事件和思绪。没有你的写作,它不存在……想和你探讨的是,尽管看上去已经一目了然了,但——什么是文学?从形而上层面,从意义上,我们考察一下,你为何会/要写作?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或者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孙智正:我喜欢好些当代艺术的想法和做法。我有个打算是以后不写诗、小说、散文、剧本,也不写“句群”了,就只写“日记”,把所有的东西收集在一块儿形成一本书叫《日记》。
我觉得“文学”首先是语言上的创造,然后是记录和开拓人类的感触。另外,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求真,就是一个个体的感触不受他人、系统、权力的遮蔽,真实地发现、真实地表达感触。
我会成为一个写作者肯定有偶然性,先天的后天的,比如我也喜欢画画但错过了,我也很喜欢听歌但五音不全,我会写东西,应该是刚好有一定的天分加上后天环境的偶合,比如写东西不怎么花钱,我家刚好又不太有钱:)。我想成为那种有原创性的“永恒”的作家,我要记录我作为人类的一个“最新”的个体活在“我”和外界共同生成的时空中的感触,这些东西都是呈现给以后可以活得更久的人看的。

《句群》,孙智正著,作家出版社 2015年9月
“一切都是记忆,都是历史”
138.游离
我要努力拨开别人的见解,发现自己对外物的见识。我站到阳台上,看到旁边的纸箱里有一些杏子,我从来都不太喜欢吃杏,但现在看到了就想吃一个,只吃一个。我把吃剩的小半个杏子扔进垃圾桶里。出门,我看到远处楼房旁边有一些特别浓烈的特别洁白的像是从地上涌起的低垂的白云。我就用手机把它们拍下来,几乎可以断定,只有在这个角度这个时刻可以看见它们、看起来这个样子。有点像也许只有在这时,耳机这首俗气的歌曲,听起来这么悲伤,让人想把它改写的那首柳永的词翻译一遍。我在江边不时在空气中看到,一群一群的飞虫,它们在空中飞着像在空中乱舞的痉挛的神经质的尘埃,它们是怎么回事,我能够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吗?我在右堤路上钓鱼时想到左堤路上看看,现在我在左堤路上一直的树荫里骑行时,越过江面能看到对面的曾经待过的右堤路,江面的电线上站着几只迎着阳光的江鸟,多么白亮啊它们的肚腹被阳光照得。
2022.8.31
严彬:你的写作和写作生活是可贵的,有一股强大的韧性在支持着你,写出了体量巨大、气质特异的作品。最近一篇你在自己公众号“多写症”上发出来的叫做《游离》的作品。时隔十六年,你这两个东西的写作气质上是一以贯之的,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表现为一种从观念到语言的恒定,也就成为你的风格。当然,2022年8月31日的这个作品,你是以一个观念开头的,你开头写到,“你要努力拨开别人的见解,发现自己对外物的见识”,接着,你开始写自己的经验……作品中的气质:游荡,直接,抒情性,让人感觉有些脆弱,美好而脆弱。小说家赵志明评价你的写作有“工匠”气质。你如何看待和理解自己这样的写作?关键性的因素有什么?如果有人说你的作品读起来荒诞,缺乏意义,或者说,很难读下去……你怎么解释或帮助他们阅读和理解?
孙智正:我不知道小平是从什么角度这么说的,应该是说我写了很久,也写得比较多。
我理解中的写作既了不起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它是人类发明的万事之一。我觉得真正重大的问题是,你怎么度过你暂存的一生。我觉得像刚才说的,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写东西成了我度过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如果没有写作,我一定也能够活下去,但可能会活得没那么充分,或者会找其他东西替代。所以这就是我会长期写的原因吧,它让我有事情做这非常重要,一种有事情做的愉快,让我有朋友、获得别人的赞扬、有吃饭的钱等。
至于你觉得我多年来写东西的风格都差不多,我也觉得有点困扰,也许是因为一个人只能提供一种方式吧,就像一个人成年后,你感觉他的性情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羡慕能提供一种以上写作风格的人,也许我只能提供一种了。
关于读者对我的作品的可能看法,我觉得他们多读两遍就好,或者让他们告诉我有什么事是不荒诞的,或者他们去看他们觉得有意义、不荒诞的东西,再回过头来看看我的东西,或者把我忘了就好。
严彬:文学创作,以及其他形式的创作,那些被称之为艺术范畴内的,都在处理各种大小的经验。经验的大小,巨大的,或是细微的,本身就是相对的。我们很难接触到绝对大的或小的事物或事件。那么,如何处理,就取决于创作者本身。你对这些自己的经验,有没有总结或抽象出某种创作理念?
孙智正:我其实没有一种清晰的理念。我有个观点是:你写什么都要想明白,要多想,但不要想得过于明白。如果一定要,我觉得个体的“知识”——“我”的感触是很重要的。阅读就是在学习别人的“感触”,但重要的是发现你自己身上的感触。如果要说知识这才是真正的知识。
严彬:能否从词语定义的角度解释一下句群、啊、史诗等这些参照以之命名的作品?它们像是被你创造的、属于你的文学专有名词,是你的概念,大概可以收录到类似我那本《后现代主义词典》中作为词条。
孙智正:《句群》就是我想创造一种新的文体,它就叫句群,看起来就是句群的样子。很难去定义它,就像很难定义诗小说散文,它往往是不分段的,又不太长,也可以很短,只有一句话。它是在现有文体之间、之外的东西。
《啊》是我觉得“啊”可能是一切语音和语义的源头,我乱说的大家不要当真,我知道写作的人会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就想以《啊》为题写点东西。本来我只是想记录颅内念头的流动,还试着给它一点逻辑,但后来发现把我以前写的微博、豆瓣广播、朋友圈直接拼在一起就可以了,我愿意接受这些载体带来的限制和启示。
《史诗》是我想记录每天的吃饭、睡觉,看到的动物、植物……其实它很抒情,所以它又有“史”又有“诗”。所以我觉得叫《史诗》是合适的,尤其史诗是个现成的词语,但它以前好像都是记录帝王将相的事迹——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不记录一个普通人(其实我不觉得帝王将相不是普通人)的事情?因为我对其他人的生活不了解,而无论如何,我还是比较了解我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记录了我的生活。《史诗》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中年》。接下来我还会写《史诗2》,既然它叫史“诗”,这次就真的会用诗体去写。
严彬:康良做了你的《句群》,特别厚,大概会有一千多页(他说有1800页!定价三百多)。三百多元购买一个很特别的作家漫长的——纵然不是整个人生——人生记录和思想,是值得的。《句群》会让我们去打量和反思自己的生活——是真的有意义吗?或者真的没有意义、碌碌无为吗?你怎么看?
孙智正:我想以前两天发的一个朋友圈来回答,感觉比较契合:一切都是人自导自演、自己观看、自己夸赞的游戏,从来没有一只鸭子对人说“你好棒棒”,但还活着就要以此度日,度过无论怎么度过都是虚度的时间。
严彬:每个人的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成为过去,或多或少成为我们的记忆,分属两种“世界”,实在的,和意识的。你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记忆的?为什么能在作品中呈现出那么多、那么长时间跨度的生活细节?其中是否有以及有多少虚构成分?
孙智正:我喜欢把话说满了。我觉得一切都是记忆,都是历史。当我们在叙说一件事时,就没有了真正的现时。在说未来时也是这样,未来都是由过去组成的。我说出的都只是记住的东西,肯定忘记了更多。
没有虚构的东西,或者没有刻意虚构的东西,都是我自认为最真实的样子记录下来的。或者说我只是虚构了形式,比如《青少年》是假装一刀不剪的长达四年的伪长镜。

《青少年》,孙智正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年10月
严彬:你写作的真诚,或者说是坦诚,令读者敬佩。很多人有写日记的习惯,下笔之前就对日记有了选择,有了审查,有些没有写,没有写出来的也许更多,不管是更好看,更重要,或者更别的什么。总之,即便是日记这种更要求真实和真诚的写作,也十分考验我们。你又是怎样从“真”这方面考虑的,经验的真和写作的真有何关联,又如何关联?
孙智正:坦白讲,我真诚或坦诚的只是一部分,隐瞒了很多。我希望等到晚年我可以写一部完全不顾忌别人和自己的东西。看过一些朋友写的日记,和你一样我也觉得他怎么这么坦诚,所以可能仅仅是有勇气(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曾写过那样的话,他说一个城邦需要人守卫,那样的人必须要勇敢;除此之外,他最好还善良。但善良和勇敢好像又是冲突的,一个善良的人很难勇敢起来。也许坦诚和真也有这样的关系和矛盾。),坦诚的部分不一样。
可能有人会说写作的真就是经验的真,我不想这么说,应该就有经验的真和写作的真。在写时,可能这个词语更符合整个语气或仅仅是因为喜欢用它,你就用了它了。但可能另外一个词更符合“经验的真”,那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前面那个词。
“我应该会一生都写东西”
严彬:除了上述那些经验性写作,近年你还依据《西游记》《八仙过海》《镜花缘》等中国古代经典作品进行了再创作。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写作?销路怎样?怎样处理原著中的材料?你的写作语言和逻辑大概是怎样的?有没有考虑过类似系统的“重新叙述古典”的计划?
孙智正:1.我想如翻唱一样翻写这些作品;2.我想如描摹现实世界一样描摹我在这些书里看到的东西,我也想描摹我们在屏幕中看到的电影和游戏。几年前我写了一个中篇《电影》,就是对我和几个朋友一起拍的电影《杀手》的复写,而《杀手》改编自我的一个短篇。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反复的复写。
原著中的材料就是我的素材。我不太会编故事,刚好可以在原著故事的基础上加入我对写作的理解和三观。把这些文本当代化,尽量融入更多我作为一个当代人的三观,要轻快,尽量不丢失原作好的地方,抛弃一些残忍的、过时的东西,基本不改动情节,只是更换语气和情绪,汇入更多个体的情感。
而对中国的古典,我没有系统重新叙述的想法,那样太辛苦了,可能那部作品你不喜欢也要翻写。这些“翻写”的作品销量会好一些,但也没好多少。这就是我的目的之一,想赚点钱,同时又有写作上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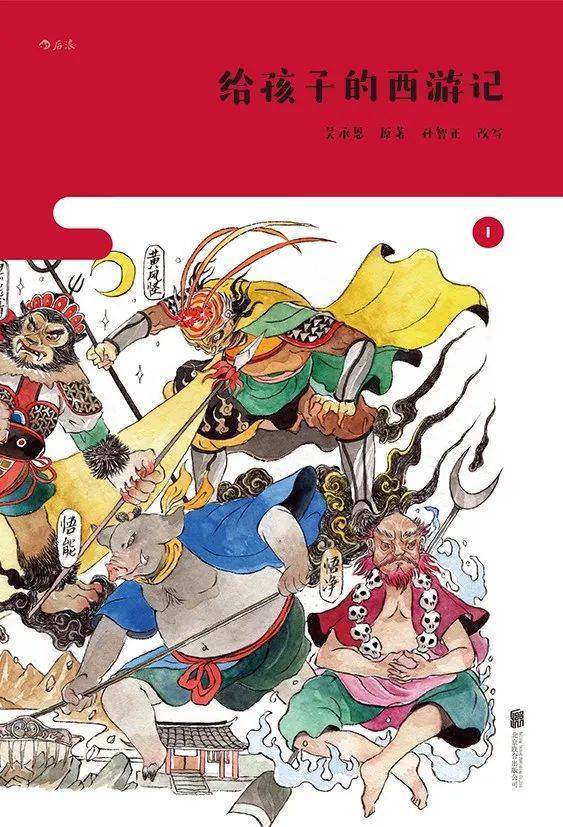
《给孩子的西游记》,吴承恩 原著,孙智正 改写,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8月
严彬:好像很少在文学期刊上见到你的作品,也许是个人及作品的特质决定了传播路径。你的作品在朋友们范围内认可度高,书籍多次在朋友的出版公司出版……如何看自己作品的传播与所谓“主流”的差异和疏离?如何考虑你的读者呢?
孙智正:其实我的中短篇大多在期刊上发表过,但可能隔得太久了发得也不够多。我没有刻意与“主流”保持差异和疏离,可能就是天生的气场不太一样,互相也都感觉到了。
谢谢韩东,我已经好久没拿到期刊的稿费了,谢谢读客的老板华楠出了我好几本书。很感谢朋友们的认可和帮助,让我觉得差不多这样也就可以了。
我让写的东西自然传播吧,因为我也没有其他办法。我深信以后我的读者会很多。
严彬:记忆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你的写作。你能否以类似“一个句群”的形式,回忆和书写一些你的童年、青少年经验——也许你的状态一直是青少年的,有一种青少年的朦胧、迷惑、新鲜与胶着,有青春气息。
孙智正:《句群18》热闹和热寂
142.童年和青少年和中年
我从家里奔跑到操场,觉得自己的双腿非常强壮。我看到太阳从操场边缘的房屋后面落下去,我觉得自己要做一番大事又不知道要做什么,后来我应该就回家了,但不是跑回去的。我在初中时经常问同学你们平时做什么事情度过时间呢,有时会骑到隔壁村的同学家外面,偷偷听他们在做什么。到了高中,星期天回家时,我会骑着车漫无目的去没有去过的地方游走。我常常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隔着玻璃,觉得自己永远从人群中穿过,我没有剧烈的喜怒哀乐。现在我躺在咖啡馆的沙发上,妻子微信提醒外面有暴风雨还有冰雹和闪电,但我戴着防噪耳塞,一点也听不到只听到咖啡馆里的人声和音乐声。知道但很难想象,“我”这个意识有一天会消失。
2022.9.4

2004年,孙智正到青岛出差。(作者供图)
严彬:对比你近二十年的几张照片,你的样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没怎么老,也没有胖,眼镜也差不多;也许心灵状态也是相近的……你怎么看自己外貌和内心的发展或变化?这和你的写作、生活,是否有某种关系?
孙智正:我自己觉得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我都老了很多。
外貌不用说了。比如内心,我觉得以前都是兴冲冲的,平静时其实都是略微倾向于开心的,现在经常觉得一切都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一切都会消失。以前当然也知道一切都会消失,但没有这样的体感,这可能就是“心灵的状态”的变化。如果说年轻,我觉得似乎会比做其他行业的同龄人年轻些,也许写作让人年轻,因为你不那么沉浸在现实中?你的生活也简单些,没那么操心?
严彬:听说你现在精力并不是那么好,常常休息。除了写作,你还在和朋友一块做旧书收购的事,然后你要将它们卖掉……可以聊一聊卖书或做书商这件事情吗?
孙智正:其实都是我朋友在做更多卖书的事情。我们经常会在打牌的路上去废品站收购一点,也从朋友那里收购。主要是做更多的自己喜欢的让自己开心的事。
严彬:你说过,“我有个想法是要用写作复制我的一生,选择我自己是因为我对我这个人最熟悉。我要一秒不差地从有记忆开始复制到我的一生。”你设想过自己的一生吗?如何生,如何死,人生的最后阶段过着怎样的生活,和他人与世界的关系……
孙智正:这就是一个说法,说法听上去总是过于完满、理想。我知道我不可能复制一生,也许以后有一种仪器,不仅能摄录影像、声音,也能摄录气味、触感和心里的所思所想以及时空中的气场,甚至包括你身体里的遗传信息……信息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竟然是有限的。所以我也不敢设想自己会过什么样的一生,比如我就不知道我会生这样的病,我只是大概地想,我应该会一生都写东西,别人会主要以写作者来定义我,可能的话我也会去拍电影。在晚年时在写《晚年》,我希望我能平静地没有苦痛地带点绝望地死去,和我自己和别人都和解了,希望留更多的钱财给自己的家人。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评论列表
- 这篇文章还没有收到评论,赶紧来抢沙发吧~



